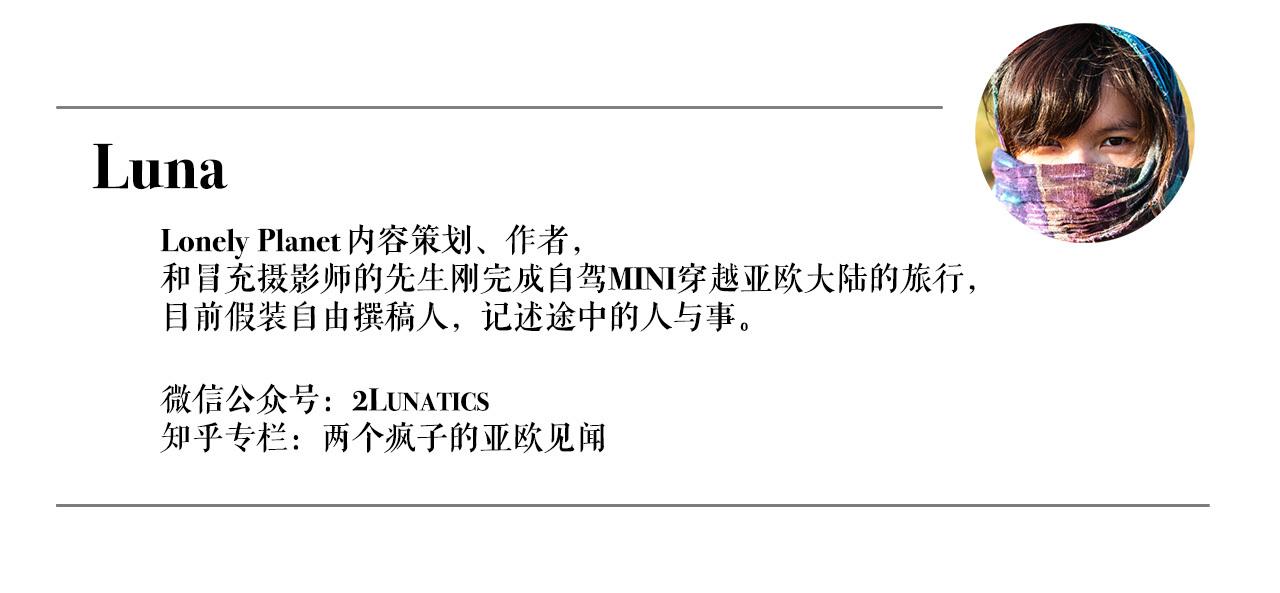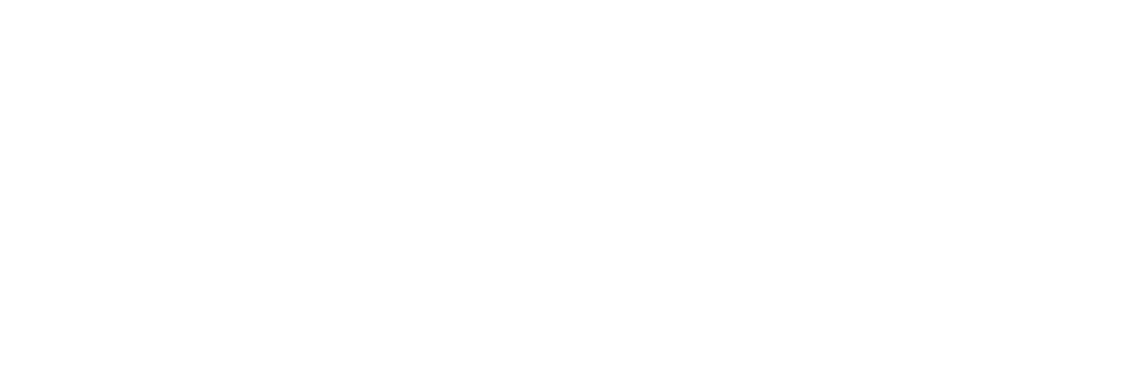不戴头巾的话,我真的会被强奸吗?
为什么到某些伊斯兰国家旅行要戴头巾?
“不戴的话,你甚至可能会被强奸。”有人这样严肃地回答。

我皱了皱眉,我当然知道危险,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在跟纪先生讨论到这个话题时,表达一下抗议:“这不合理,我并不信伊斯兰教,我只是个旅行者,为什么非得打扮成一个穆斯林的样子?而且如果我信奉基督教、佛教、道教、随便什么别的宗教,这不是有违我的信仰吗?”
“那么你可以选择不去伊朗。”
我知道再说下去就会开始没完没了的争吵,但我那会真的赌气不想去伊朗了。
在自驾亚欧的漫长行程中,我们一路上只经过三个伊斯兰教占主流的国家,土耳其、伊朗和哈萨克斯坦。其中只有伊朗规定了旅行者的着装,女性必须戴头巾、上衣遮住臀部、不能露腿、不能显露身材曲线。这让我感到很不适,遮盖头脸、甚至全身的穆斯林妇女着装一向被我视作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

那时候我们刚进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街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带头巾、裹在黑袍里的妇女,甚至有的连脸部都遮住,只露出一双眼睛。这让我感到不安,仿佛袍子里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那些日子土耳其的安全局势也不太好,我知道自己只是非常片面、毫不公正的刻板印象,但总止不住联想到早些年自爆的“圣战”黑寡妇。

除了少数本地人外,这些黑袍蒙脸的女性大多是游客,三三两两聚集在景点门口拍纪念照。这也让我感到不解,照片里从头到脚一片黑,除了眼睛完全看不出长相,拍了又有什么意义。
“她们可能是从要求更严格的阿拉伯国家来旅游的,”纪先生推测说,“这些政教合一的国家的更加保守,相比而言,土耳其是个世俗化的国家,她们想来这放松、享受一下现代生活吧。”

连黑袍子都不敢脱下的现代生活吗?我撇了撇嘴。
根据教义,妇女除手和面孔以外均被视作羞体,露出头发和脖子,跟露出大腿、屁股的性质没两样,因此要求女性在公开场合必须遮盖除脸和手的其余身体部位,常见的遮住头发和脖子的头巾(hijab)就是这样一种服饰,更保守的是遮盖全身的罩袍(布卡,burqa)。

土耳其虽然普遍信仰伊斯兰教,但理论上实行政教分离,尤其是伊斯坦布尔和爱琴海沿岸的几个城市,短裙、短裤颇为常见,大概确实能让她们体验一次现代生活吧。
我们在全球连锁的服装店里也看见了一些黑袍妇女,她们正在选购颜色亮丽的裤子和T恤。可能是某种本土化特供的策略,伊斯坦布尔的Zara和H&M有很多印着腰果花纹的长裤,这是典型的伊斯兰风格的设计,而我试图在全球网站和天猫上查找,都没有看见这些款式。
但即便买了,我们也没机会看见这些女性穿着,再时髦的设计都被她们裹在了黑袍下面。哪怕是出国旅行,她们也不敢对自己的服装松懈分毫——在国外脱下头巾拍了照,后来被本国人发现,受到惩罚、甚至死亡威胁的例子不要太多。

这让我对头巾的象征意义愈发不满。虽然教义并没有说明女性的穿着如果未能遮蔽羞体会怎样,但一部分人将其解读为:这样的女性应该受到惩罚,由之而来的性骚扰、强奸、乃至谋杀,都是自找的。这种歧视女性的想法,在我看来实在是落后又愚蠢。
从土耳其陆路进入伊朗时,我和许多人一起在土耳其海关盖好章,然后往前走的过程中,妇女们纷纷从包里掏出头巾系上,我虽然不高兴,但也不得不照做。走到伊朗海关前面时,我的头巾有些滑落,海关人员示意了一下,看着我整理好了,便盖章放我过去。

在德黑兰的第一天,我们住的酒店房间里只有浴室,厕所是公用的,在屋外的走廊边。哪怕我半夜起床上个厕所,都要戴上头巾。
抵达亚兹德时,我们遇见了一对从山东来旅行的兄妹,妹妹年纪与我们相仿,跟我一样裹一条围巾当头巾,在炎热的7月闷出了痱子。
但我发现许多伊朗女性似乎也有跟我们一样的烦恼。

在政教合一的伊朗,戴头巾的女性大抵可以分成三种:黑头巾黑罩袍的女性并不多;普通着装、黑头巾遮住全部头发和脖子的稍多;戴着花头巾的则更常见——许多只是随随便便一搭,像个装饰品,浓密的头发依然露出来,衬托出波斯女性如同雕塑般的美丽面庞。她们大概也不喜欢头巾这玩意,既然不得不戴,那就只能戴得尽量好看一些。

这也难怪。伊朗并不一直都是宗教保守的国家。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的上层社会非常西化,性别隔离和黑罩袍都是被禁止的,妇女拥有投票权及婚姻平等。革命之后,许多女性被迫戴上头巾,数以万计的人被投进监狱,西方的一切——从服装、酒精到音乐,都被禁止。

我想在这里推荐一部根据同名绘本改编的电影《我在伊朗长大》,讲述了作者还是9岁女孩时亲历的伊斯兰革命,以及她在那之后的身份挣扎——最终,这个在伊朗长大、在欧洲留学的女性发现,尽管自己是个地道的伊朗人,却无法在这个国家生活。

如今,伊朗依然有人在偷偷怀念着伊斯兰革命前的自由生活,或者说向往着更开放的社会环境,人们在私底下悄悄地“反抗”。德黑兰的汽修店挂着奔驰和宝马的LOGO,加兹温的咖啡馆画着好莱坞的电影海报,这些都成为他们对西方与更世俗的生活的一种想象。女性想办法在头巾上钻空子,就像许多家庭在偷偷酿酒、许多年轻人在偷偷听摇滚音乐。
这像是一场抗争。多一些色彩和花纹意味着战线的推进,多露出一缕刘海意味着一场战役的胜利,而被宗教警察抓住则意味着一场失败——戴头巾的尺度一直在变化。

一个伊朗男人在伊斯法罕告诉我们,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东西,而他并不喜欢阿拉伯人的那套规矩。我望了望一旁带着孩子玩耍、黑色头巾遮住头发与脖子的妻子,不知道这句话有几分真、几分假。

我们所拜访的伊朗也由此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一些朋友提醒我千万要小心,她们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被伊朗男性摸大腿、拍屁股的性骚扰,以及被宗教警察警告要戴好头巾的情况。
另一些则对伊朗有着非常良好的印象,被邀请进入伊朗人家做客,喝私酿的酒,看见女性取下头巾、换上热辣的紧身裤和吊带衫,与她们一起唱歌跳舞开派对。
我无法判断上述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常见,它们都是这个国家的真相。

也因为对头巾的态度,我感到伊朗社会某种程度上的割裂。在富裕的德黑兰北部,有许多高级的酒店和餐厅,参与到社会上各种工作的女性也非常多,她们都打扮得优雅得体,头巾只是她们秀发上的一道装饰品。
而在宗教保守的卡尚,女性的穿着要严格得多,我没有见到一名戴花头巾的女性。

这让我想到另一部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中产阶级的女性穿着简洁,头巾随意一裹,露出红色头发,每天都要上班;来自社会底层的女性全身黑罩袍、黑头巾,偷偷出来当护工补贴家用,还必须瞒着丈夫。当护工帮助失去行动能力的男性老人擦洗身体后,她感到了极端不安与恐惧。贫富的差距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区别,还有对待宗教的态度。

虽然伊朗远不是中东最保守的国家,伊斯兰教还是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界限,也限制了女性旅行者在这个国家的活动范围,使得在伊朗的女性旅行者和男性旅行者也有了完全不同的体验。
男性可以去传统的伊朗茶馆坐坐,但女性被拒绝入内;乘坐地铁时有专门的女性候车区和车厢,作为对女性的“保护”;男性可以与热情的伊朗人握手、拥抱,但女性不应该与他们有任何身体接触;还有一些旅馆会拒绝接受独自旅行的女性入住。

第一次是在伊斯法罕的大巴扎里,自称琐罗亚斯德教(中国人更熟悉的名称是拜火教)教徒的商人,表示我可以在他的店里取下头巾,放松一下,因为在私人领域他并不需要遵守伊斯兰教法。
巴扎里有专卖头巾和罩袍的商店,颜色、花纹多种多样,有些材质极好,售价也不便宜。但再怎么精美,想想其含义,我便欣赏不起来。

另一次是在琐罗亚斯德教的发源地亚兹德,向导带我们穿过沙漠去看圣地和祭坛,车行至荒无人烟的沙漠中时,他对我们说:“现在,你们如果想的话可以取下头巾,吹吹风凉快凉快,这里没人能看见你们。”
这时候我反而不想摘下头巾了,沙漠里阳光强烈、风沙极盛,头巾能帮我遮阳挡风,确实很有实用性。

“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那是个沙漠地带,有可能早在这个宗教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根据环境而穿成这样了,宗教只是延续和稳固了这样的服饰。”纪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
然而,当伊斯兰教传播开来,要求非沙漠地带的女性也戴上头巾的时候,服装便不止是服装了,而更多具备了宗教和社会意味。

将露出头发视作羞耻不再是由生存环境决定的了,而成为一个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在这个规范当中,女性是被歧视、被限制的。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宗教并没有随着时代进步,还跟古时候一样依然在剥夺女性选择自我着装的权利。
随之而来的,是教育、工作各方面对女性的限制——一些理工科专业的实验要摘下头巾才能安全完成,一些工作也要不戴头巾才能安全进行,至于像护工这样需要接触男性身体的工作,则更有争议了。

至于一些人所理解的,女性必须降低自己在衣着方面的性吸引力,才能阻断男性不正常的念头,这种典型的对女性的物化,跟“你打扮得太美、活该被强奸”的混蛋思想没有两样。
教义的规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自我的认同。许多伊朗女性即便出国留学和移民了也戴着头巾,许多穆斯林女性一开始没有戴头巾,后来因为家庭、朋友中许多人戴便也跟着戴了,这成为她们对自己的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的一种外在象征。人始终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一个保守的伊斯兰社区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压力。

头巾也成为一种安全感的来源。当你身处保守的伊斯兰社会,如果社会氛围中表现出,不戴头巾的女性应该被轻视、被警告,那么你将不得不戴上头巾,以保证自我的安全。一些伊朗人只有把自己的妻子、女儿包裹在头巾里后,才敢送她们去工作、去上学,走进公共区域。一些伊朗女性只有戴上头巾以符合整体社会规范之后,才敢放心地参与现代生活。

这大概也是女性旅行者不得不在伊朗和其他一些更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戴上头巾的原因——一方面,这是宗教法规定的,无论多么不合理,违法也是不被推荐的;另一方面,为了自身的安全,我们不得不假设社会的部分男性是潜在的强奸犯。
本文首发于我的微信公众号:2Lunatics
知乎专栏:两个疯子一辆车的亚欧之旅——讲述自驾环游亚欧331天、25国的故事